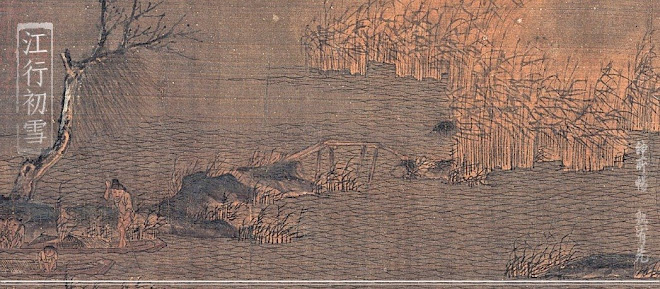還記得當年修德文課,有個自由選題的德國文化短篇報告,我挑了德國白酒。Spätlese、Auslese、Beerenauslese…就靠著這些看似深奧的專有名詞,在台上胡吹亂蓋,順利過關。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,現在能記住的德文也只剩下這幾個,理由很簡單,實用。
今晚全系列德國白就從93年的Spätlese開始喝起,Brauneberg丘打頭陣,根據記載,這區田地在十九世紀末賣得比Krug vintage還要高,但不知道當年賣的是什麼級別?這支Max Ferd. Richter莊,酒色相當年輕,仍是亮嫩的檸檬黃,果味清新,Mosel牌的汽油味不甚明顯,甜味因為年歲已經降到適口程度,漂亮的開場。跟著的一支Robert Eymael 92’ Spätlese,果味全被第一支吃掉。
再來淺嚐貴腐菌味,Auslese級別,結構與力度明顯的提升。首支是Oberemmeler Karlsberg,von Kesselstatt家族釀造,這家子釀酒歷史竟可以推到十四世紀,曾當過宮廷酒水大總管,掌管皇家果園與酒窖。從這支酒的平衡度來說,感覺得出此莊雄厚的功力,香氣由葡萄產生的豐富citrus味、陳年散發的汽油味、貴腐菌帶來的複雜蜜香三面融合,不偏重任何一方,入口細緻滑順,糖份雖然較重,在酸度的催化下沒有一絲膩人的感覺,收尾一抹焦糖味再添層次,89年份,可說正進入高峰期。
做為對照組的另一支89年則是一支冰酒,Oppenheimer Guldenmorgen,比較的重點當然就是有無貴腐菌參與的差異性。冰酒靠的是霜凍截去水分,嚴謹的德國佬規定,一定要在零下八度採收製造才准貼上冰酒標籤販售。這個八度到底怎麼定出來的實在令人費解?但每想到採收工人要在寒冬的清晨搶收榨汁,這杯中美祿可謂粒粒皆辛苦,足顯珍貴。如果說貴腐味總是帶著嬌艷氣質,冰酒則能稱做一派甜美,沒有難以捉模的神秘,不擺架子,讓人不自禁陷入的愉悅。香甜味濃,有若混入了各式堅果與蜜餞的焦糖餡餅,誘人咬上一口。
慢慢進入高潮,來到了Beerenauslese層級,再度回到Mosel區,年份下探76’,這支Ewald Theod. Drathen酒莊的Alfer Kapellenberg坡,色若琥珀,用了德國近代混種Huxelrebe葡萄,這酒莊、區域、葡萄種都算罕見,入口更讓人驚訝。BA也不是第一次喝,但首次發現到如此輕盈的口感,酒在嘴中擴展開來,在舌上顎間舞起了芭蕾,好似在每一處角落,你都能享受那份美感。沒喝過年輕的Huxelrebe,此葡萄的底細無從體會,但是下一瓶69年Frauenberger的Riesling BA竟被硬生生比了下去,倒地不起。其實Huxelrebe並不是什麼優秀品種,這時心中生了疑問,莫非德國老貴腐的年份因素要大於品種?
正式端出TBA,來自Pfalz的Schweigener Sonnenberg坡75年,酒莊仍是Ewald Theod. Drathen,葡萄換成了Ortega,也是混種,讓人納悶這間莊園是為了省成本還是富有實驗精神?不過適才那隻BA已然表現不俗,不容小覷。以往幾次TBA的經驗都感覺有些稠膩,風味當然是沒話說,卻無法多喝。這支老TBA挺適口。沒有甜過頭,口感相當chewy,香氣上除了果味、揮發劑,還含有一股清甜的生甘蔗味,入口後太妃糖的氣息漸漸散出,相當結實的一款酒。
壓軸的酒從一開始就讓人期待,因為是71年,半世紀來德國白酒的超級年份,仍是Pfalz區,Dürkheimer Hochbenn,酒莊是Freudenmacher,正牌Riesling,酒色已相當深沉,頗似冬瓜茶。微微晃杯,香氣是撲面而來,到底是什麼味?喝到這裡其實已經懶得分析,可以說該有的她都有,姑且就叫它TBA味吧。入口後,發現剛才的律動感又來了,這次的舞步更為純熟,教人神魂顛倒的風韻從舌上直吸入腦門,喝!好一個強身健體的迷幻藥。
TBA,全稱Trockenbeerenauslese,如果你一句德文都沒學過,這是個值得記住的詞,20個字母,花上20分鐘都未必能解釋清楚是個什麼玩意兒,唬人自用兩相宜。
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