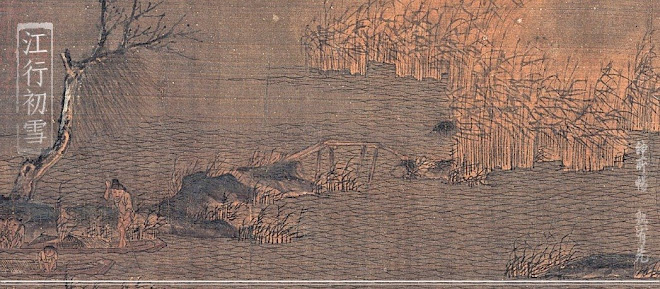左鄰藏有南亞菜高手一名,每日時辰一到,必有陣陣致命香氣飄出,動魄迷魂且變化多端,逢周末假日尤甚,若空腹以對,後果不堪設想,已然構成嚴重公害。但在家燒菜又不犯法,你奈我何?想想只能偶爾與以反擊,家中兩鍋老滷,一鍋燉豬腳,一鍋醬牛肉,任你是信伊斯蘭還是印度教,總能讓我扳回一成。
在倫敦做醬牛肉,標準得放低,想找安格斯黑牛腱心?恐怕要到Smithfield Market與牛攤老闆廝混好一陣子,豈有這等閒工夫?中國城偶然買到筋多勻稱的腱子已心滿意足。至於配料這等樂事決不能假手他人,我廚房從來沒有現成滷包,但也犯不著用什麼新會老陳皮、漢源大紅袍一類上品,求全不求精,基本五香大料俱備,荳蔻、草果、砂仁、山奈…種種偏方也齊,每當要製滷水,構思再三,東抓西揀,發洩自我創作慾罷了。
還有一樣東西不容妥協,醬油。選醬油這點雞毛小事有何重要?每想到這個嚴肅的問題,心又擰了一下,好像現在沒人在乎醬油是怎麼做的?吃的人不講究,做的人何費工?看店裡滿是速成產品,狠點的用強酸溶解大豆再對鹼還原,不然就是另添人工胺基酸,胺基酸可以是各種來源,雞鴨鵝毛樣樣可製,只要嚐來又鮮又鹹色黝黑,已經符合醬油在近代文明的定義。事情的嚴重性快提升到文化國格的層級,試想將來有一天還要派人到日本學習傳統醬油怎麼釀,誰能再吹噓中國菜世界第一?
倫敦的難處在於選擇太少,台灣方面偶見金蘭醬油上架,勉強用之,或是託人帶西螺產純釀醬油;香港品質好點的多半是生抽,不適燉煮;大陸能出口到這來的牌子幾乎不考慮;馬來西亞生曬油只能用來頂醬色,懶得炒糖時加它兩匙;日本醬油,也不是罐罐天然,要尋古法手工釀造熟成壹年以上者,並非沒有,可惜成本過高。總之選醬油一向是個傷腦經的事,但是絕對有文化上的道義責任。
滷水最引人入勝的美好特質,在於越陳越香,滷味鋪子失火,第一個搶救的肯定是那鍋滷。家裡那年近兩歲的滷兒,從小也受百般呵護,肉料必須去盡多餘血水,調味則務求一致,更忌雜混食材,亂滷一通。家中無法天天滷,存於冷櫃,冰凍之前要撇油濾淨,三不五時還得取出煮沸。如此細心照料,養得通達靈透,常在鄰里間揚眉吐氣,更滿足了不少人的胃。無奈天下無不散筵席,將來恐怕還得找個有緣人認養,一鍋流落在倫敦的老滷,不知其未來命運如何?

(本月宴客造型,搭以簡版芥末墩)